首页 > 甘肃文化 韩国短剧,摸着中国过河
韩国短剧,摸着中国过河
在这个注意力稀缺、时间被切割成秒的时代,短剧成了全球影视业的一种“新语言”。
它速度快、成本低、传播广、反馈即时,像是影视工业的“快餐化革命”。
或许短剧的开创者们也未料到,这场革命最早从中国出发,却迅速开始了自己的“国际化”进程,东南亚和北美的火爆就不多说了,如今,连以高制作、高标准著称的韩国,也未能免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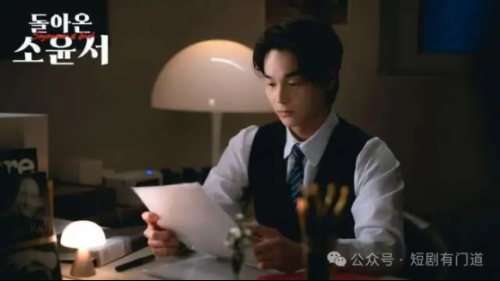
(△ 苏夜的复仇)
去年底,出演过《信号》《当你沉睡时》的韩国知名演员李相烨,出现在了一部仅几分钟一集的短剧里,剧名叫《以爱为契》。
与此同时,另一位观众熟悉的名字——前女团PRISTIN成员朴施妍,也因为出演大尺度短剧《不得不做的室友》登上热搜。
这部作品里充满了“十九禁”的桥段:接吻融冰、胸口夹气球、夜宿共眠,尺度之大,让不少人表示相当“震惊”。
甚至有相当的粉丝开始抗议,认为这种大尺度剧情,影响了自己爱豆的前途。
嗯,柳五劝你们别多管闲事。
这不是个别现象,而是韩国影视业的一次集体转向。
短剧,这种起源于中国、被全球模仿的“微型影视形式”,如今正成为韩国娱乐产业新的实验场。越来越多偶像、二三线演员,甚至知名长剧演员,开始频频出现在竖屏短剧中。
韩国短剧的数量,在短短一年内暴增,从2024年的二十多家制作公司,飙升到如今的上百家。
短剧不再是小众尝试,而是正逐渐成为韩国影视界的一股新潮流。
idol与长剧演员纷纷下场,十九禁题材、狗血反转轮番上阵,看似热闹的背后,其实是一场全球影视产业的深层震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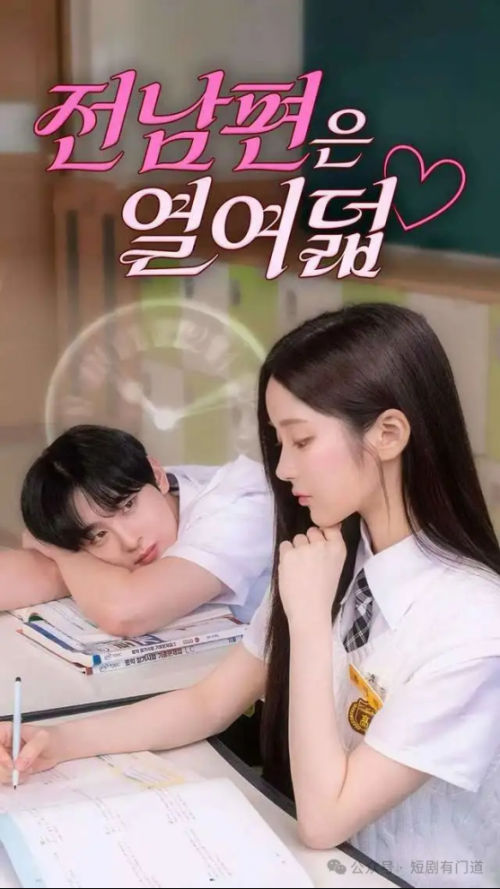
(△ 前夫十八岁)
韩国短剧的崛起,其实是一个“不得不”的结果。韩国的长剧体系非常成熟,从编剧到制作都有严格的工业链条,但正因为如此,成本高、周期长、风险大。
对投资人来说,每拍一部韩剧都像是在豪赌。
而短剧提供了一个更轻盈的出口——拍一部成本可能只有韩剧的百分之一,但如果运气好,一个爆款就能赚回整年的支出。
它是一种更适合当下互联网生态的“快速试错”机制。
而且,韩国短剧的爆发还有一个明显的推力:偶像产业的衰退。
大量idol组合解散、成员转型受阻,他们急需一个重新亮相的舞台。
短剧,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低门槛、高曝光的机会。
朴施妍、李相烨这样的名字出现在短剧里,乍看是“自降身价”,但从产业角度看,这其实是一次再就业。
过去,偶像靠唱跳和综艺维持热度,现在靠演短剧争取镜头,流量逻辑没变,只是媒介换了。
这都已经是国内的娱乐圈走过的路,韩国,只不过再重来一遍而已。
短剧,终于还是成了韩国演艺圈的“蓄水池”。
那些不再登上音乐节目、拿不到长剧资源的艺人,纷纷涌入这个新市场。
制作方也乐于接受这种流量互换:偶像带人气,平台给曝光,观众买单,哪怕剧情狗血、制作粗糙,只要能刷屏,就是胜利。
某种程度上,短剧已经成为“后韩流时代”的一张门票。
但更深层的逻辑,是整个全球影视行业都进入了“低潮期”。
流媒体大战烧完钱,观众被算法宠坏,没人愿意再花十几小时追一个故事。
Netflix、Disney+都在裁员、降本,而短剧正好迎合了这种现实:
它不讲究结构的宏大,只要三分钟内有冲突、有反转、有情绪,就能成立。
韩国短剧也在延续这种“速食叙事”的逻辑——
爱情、复仇、欲望、伦理,所有戏剧元素,都被压缩成快餐式的情绪爆发。
如果说十年前韩剧是浪漫的代名词,那么今天的韩短剧,更多是躁动与暧昧的象征。
题材上,它们正迎合算法世界的口味:十九禁、狗血、反转、伦理擦边……
比起精致叙事,它更像是一种感官刺激的堆叠。
《不得不做的室友》《订婚风暴》《再见,哥哥们》这些作品,不需要太多逻辑,只要足够“上头”。
韩国短剧不追求共情,而是追求瞬间的点击。
而相比国内,韩国对影视作品更大的宽容度,也让短剧这种形式,在那边有了更多可能(柳五表示很羡慕)。
这种转变,恰恰是时代的映照。
全球电影票房低迷,长剧疲软,观众碎片化的注意力正在重塑影视生态。
短剧的浓烈情绪表达,正如社交媒体上的人类情感:零碎、急促、无处安放。
根据相关报道,近两年来,韩国的短剧制作公司正在疯狂扩张。
2024年还只有二十多家,如今已超过一百家,从idol公司、广告公司到传统电视台,几乎人人都想分一杯羹。
但问题也随之而来:韩国短剧本土市场,实在是太小了。
韩国人口不到6000万,短剧用户不过一百万人。
大家都在拼命做,却都赚不到钱。
于是,“出海”成了唯一出路。
嗯,这个思路,跟中国的短剧市场,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区别在于,国内是实在卷不动了,只好出去卷老外。
而韩国恰恰有韩流加持,语言壁垒反而成了文化符号。
全世界已经习惯了韩语的听感,从韩剧到Kpop,从BTS到《鱿鱼游戏》,韩国内容早就形成了天然的全球亲和力。
韩国短剧在海外的机会,就藏在这份“文化惯性”里。
但短剧要“出海”,靠的不是文化深度,而是情绪的普世性。
无论中国、韩国还是欧美,短剧都在讲同一个主题——“命运反转”。
穷人变富、被甩者复仇、前任后悔、爱情得偿,这些故事简单到极致,却击中人类最原始的欲望。
短剧的流行,其实是人类情绪被算法精准分发的结果。
短剧之所以能走出国界,是因为它不需要翻译。
哪怕你听不懂韩语,看着男女主打情绪牌、表情夸张、剧情极端,也能立刻理解发生了什么。
它是一种“无国界叙事”。韩国短剧的“出海梦”,本质上是全球化下的“算法共鸣”。
当然,这种趋势,也没那么值得欣喜。
当影视创作被算法绑架,当演员的存在只为流量,当剧本成了模板堆砌的流水线产品——艺术感正在被“点击率”取代。
韩国短剧如今的狂热,其实像极了几年前中国短剧的1.0阶段:人人在拍,人人在赚,人人都在重复同一个故事。
不过,毕竟这种形式,为全球的年轻创作者打开了一扇门。
过去拍一部剧,需要专业团队、大资金、大平台背书。
现在,台FX3、一个三脚架、几个演员,就能拍出几十万、上百万的播放。
短剧的意义,不再只是娱乐大众,它还在悄悄改变影视行业的权力结构。
那些原本进不了门的年轻人,至少有了举手的权力。
显然,全球影视产业,都在上演一场“去中心化革命”。
大制作的神话正在坍塌,碎片化的表达正在接管舞台。
未来的影视世界,也许不再是好莱坞的、也不再是奈飞的,而是被成千上万条短剧共同拼出来的。
韩国短剧的故事才刚开始,而中国短剧,已经帮所有人打了个样:
长与短本身并不重要,只是看你有没有更好的想法。
干就完了思密达!
责任编辑:
文章来源:http://www.ruyigansu.com/2025/1109/20027.shtml
